摘要: 《西狭颂》似乎在寻求外拓与中含的结合点,故显得放而不纵,含而不止。该碑又是汉隶中方笔运用的典型代表。方笔太多,易于结板,故掺以篆势,使其古雅;或加入楷法,求于灵动。此亦应了刘熙载《艺概》所谓“隶形与篆相...
原标题:《西狭颂》的书与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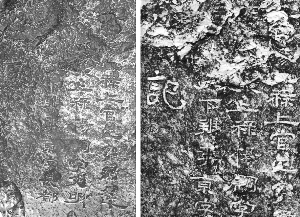
《五瑞图》下题名

《五瑞图》

蔡副全
《西狭颂》书法艺术
《西狭颂》摩崖集篆额、正文、题名、题记及刻图为一体的完备形制,在历代碑刻及摩崖石刻中极为罕见。其书法艺术为中外书家所称道。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谓其“宽博遒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赞其“疏宕”,杨守敬《评碑记》誉其“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徐树钧《宝鸭斋题跋》叹其“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梁启超《碑帖跋》颂其“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日本牛丸好一甚至称它为“汉代摩崖的最高杰作”。在我看来,《西狭颂》书法艺术特征可以从“方正”、“宽博”、“静穆”三个方面去理解。
1.方正
杨守敬《评碑记》称《西狭颂》“方整雄伟”。《西狭颂》正文二十行,满行二十字,纵145厘米,横145厘米,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而正文中绝大多数字形是正方形的,这在汉隶中极为少见。相同周长的矩形有无数,而正方形只有一个。所以,正方字形的结构处理是有一定难度的。是从中国方块汉字的发展历程看,篆书(小篆)字形长方,取纵势;隶书(八分)字形扁方,取横势;楷书(唐楷)字形长方,取纵势。故汉字外形发展经历了“长方”—“扁方”—“长方”的演变。在此演变中,正方字形的出现就显得比较独特了,如汉隶之《西狭颂》、《郙阁颂》、《张迁碑》,唐楷之颜真卿《麻姑仙坛记》、《颜家庙碑》等。
《西狭颂》的“正”,是一种质朴的平正,故显得大智若愚。关于“平正”与“险绝”的辩证关系,孙过庭《书谱》论述尤为精辟:“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清人吕世宣对《西狭颂》书法是这样评述的:“结体甚平,平近板;运笔甚缓,缓近弱。伊墨卿先生祖此,然非善学者。学此等书须从篆笔求之,须以险笔出之。依样葫芦即为所误。书以韵胜,尤以气胜,舍气求韵便弱,而无骨虽文亦然。此碑韵却极好。”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由此可知隶书笔法多作外拓,而《西狭颂》似乎在寻求外拓与中含的结合点,故显得放而不纵,含而不止。该碑又是汉隶中方笔运用的典型代表。方笔太多,易于结板,故掺以篆势,使其古雅;或加入楷法,求于灵动。此亦应了刘熙载《艺概》所谓“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
2.宽博
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称《西狭颂》“宽博遒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此碑“疏宕”。宽博,是在书艺结体领域里与“紧结”相反相形的美学范畴。“宽博”在唐代已成为常用的书艺品评标准之一。李嗣真《书品后》说“钱氏小篆、飞白,宽博敏丽,太宗贵之。”张怀瓘《书断》中说张融“宽博有余,严峻不足”。
就一个字的方块空间结构来看,如果说紧结美表现为内聚外舒,那么宽博美则表现为外满内疏,特别是中宫的虚疏。
宽博和方正是交叉的概念,在有些作品里,方正就是宽博,宽博就是方正,如《西狭颂》、《开通褒斜道刻石》、《郙阁颂》、《衡方碑》等。但是,有些宽博者就不一定方正,如《泰山经石峪》。
《西狭颂》的宽博和方正是一致的。其结字外紧内松,中宫疏宕,故显得大气磅礴。此碑结字,未作大疏大密的对比,而是信手拈来,平淡处之。碑中笔画繁者使其简,笔画简者饰增笔,或以俗体代之。
3.静穆
中华民族是主静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主静的文化。儒家讲“中庸”“中和”,道家说“涤除玄鉴”“物我同化”,佛家的“渐修”“顿悟”都渗透了以静为主的文化观念。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说“不懂中国书法,就不可能懂得中国艺术”;旅居法国的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则强调:“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书法是文化核心的核心。”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自然也与“静”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狭颂》的方正与宽博正好映衬它的静穆。毋怪乎梁启超《碑帖跋》称《西狭颂》“雄迈而静穆”。
早在商代,人们就对方形、圆形有着亲切的知觉把握和热烈的关注。《孙子·势篇》写道:“木石之性……方则止,圆则行。”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云:“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作为基本形,“圆”在人们的视觉中有着转动之势;“方”在人们的视觉中有着安静之势。这是人们视觉经验历史积淀的结果。
静美作为一种具体的审美形态,如潭水映月、幽谷流泉、鸟鸣空山……它给人以心旷神怡的美感,若反映到书法作品中来,会使人获得更深的艺术享受。表现在书法实践方面,书法静美是一种含蓄、内力的体现。不过“艺术作品的静谧乃是动态的静谧而非静态的静谧”。《论语·雍也》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西狭颂》摩崖至今碑立原貌,背山面池。此谓“环境之静中寓动”。《西狭颂》“正文”为标准正方形,规整隶书——静。其上篆额(弧线)——动;其右《五瑞图》画像(弧线)——动;其左“十二行题名”(书写随意)——动。此谓“形式之静中寓动”。
《西狭颂》作为汉隶成熟的典范代表,其笔法表现出:“方”“顿笔”“外拓”“雄强”等特征,即“静美”。而碑中篆意和楷法的运用,则使其有动感。此谓“用笔之静中寓动”。另外,《西狭颂》结字的收与放,字形的变化与统一等,都处理得自然贴切,天衣无缝。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书法静美在艺术意境中是一种无言之美、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它是一种纯美、真美,是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五瑞图》与汉代祥瑞文化
《西狭颂·五瑞图》是汉代典型的“图谶”祥瑞。
祥瑞也称“符瑞”,汉代祥瑞文化源于“谶纬之学”和“天人感应说”。“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谶,《说文》译为“验”,也就是预言、预兆,可分“谶语”和“图谶”两种。“纬”是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将“谶”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由于谶纬的目的是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与兴废,所以图谶也多为祥瑞的征兆,直称“符瑞”。汉代祥瑞思想的盛行与董仲舒“宗儒”关系极大。董仲舒提出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汉书》卷七七《刘辅传》讲:“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无神论者王充对所谓的“祥瑞”是持否定态度的,其《论衡·是应篇》云:“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其《论衡?指瑞篇》又指出:“且鸟兽之知,不与人通,何以能知国有道与无道耶?人同性类,好恶均等,尚不相知,鸟兽与人异性,何能知之?”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王充的反对并无多少人响应,而是信奉祥瑞的人越来越多,从朝廷到民间,对祥瑞都非常重视和迷信。甚至在官方修纂的史书中,专门列出祥瑞的卷目。如《宋书·符瑞志》《魏书·灵征志》《南齐·祥瑞志》。《汉书》《后汉书》虽未专列门类,但在“本纪”与“志”中也多次提及。
除了“谶纬之学”和“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外,东汉祥瑞思想的盛行还与朝廷对祥瑞现象的“嘉奖”有关。东汉元和之后,朝廷诏书明示,凤凰、黄龙等祥瑞出现亭部,不仅要减免租赋,还要给地方官员及所见者加爵授赐。《后汉书》卷三《章帝纪》云:“(元和二年)九月壬辰诏: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
早期的祥瑞思想还比较零碎且不系统,到了东汉已构成了较完备的体系。这在汉画像石(砖)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汉画像石的分布地域非常广阔,大致可划分为四大区域。一是以山东徐州为中心的苏北、皖北、豫东区。二是以河南南阳为中心的豫南、鄂北区。三是陕北、晋西北区。四是四川、重庆、滇北区。李发林先生曾对汉画像所见“图谶”祥瑞作过统计,其种类多达36种。甘肃陇南成县的《五瑞图》摩崖画像,从地域上看,偏离于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区之外;从形式上看,则表现为摩崖线刻,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表现内容依然是典型的“图谶”祥瑞。《五瑞图》画像有嘉瑞(黄龙),大瑞(甘露降),上瑞(白鹿)和下瑞(嘉禾、木连理)等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祥瑞含义。《宋书·符瑞》记载:
黄龙者,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鱼,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
白鹿,王者明慧及下则至。
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
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穟,于夏德,异本同秀。
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生。
《五瑞图》艺术特色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宋曾巩《元丰题跋》谓:“近世士大夫喜藏画,自晋已来名能画者,其笔迹有存于尺帛幅纸,盖莫知其真伪,往往皆传而贵之。而汉画则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图(《五瑞图》)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然后汉画始见于人。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伪也。”清杨守敬《评碑记》称:“《五瑞图》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画法飞动,尤殊观也。”晚清学者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写道:“陇上汉刻皆在流沙以西,关内惟成县天井关有《李翕西狭颂》。”并赋七律称《五瑞图》为五梁祠画先声:“鸾翔鹤翥下苍冥,析里桥头古勒铭。笙磬音同周雅颂,衣冠制出汉丹青。八分自得天然妙,五瑞相传地效灵。黄龙白鹿木连理,五梁祠画有先型。”
《五瑞图》摩崖画像采用汉画像石常见的散点式构图和分层式构图。五瑞分居两层,黄龙、白鹿居上,二者穿插呼应,动静结合,错落有致。木连理、嘉禾、甘露降(承露人)一列在下,四者高低起伏,疏密有度。《五瑞图》构图遵循了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动与静、疏与密等美学原则,其布局合理,变化自然,主题突出,给人以疏朗、明晰、舒适之感。
黄龙,居左上方,约占画像三分之一,呈“S”形,蛇头豹身,身布鳞纹,昂首舞爪,作腾跃状。在黄龙后足部另刻“C”形云纹(一说为“小龙像”),线条简约,依稀可辨。黄龙上方榜题刻“黄龙”二字。在河南、山东及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或画像砖,也多有龙的形象,如应龙、黄龙、青龙等,这些龙的形象因受材质的面积的限制,其外形多作适合形处理,体态为“S”形盘曲状,或在四周饰以云纹、飞鸟等。
白鹿,立于黄龙右侧,体态丰健,扬首前视,神态安详。鹿角上方空处书“白鹿”二字。《五瑞图》之白鹿,形象生动而写实,运笔柔中带刚,虚实相生,转折自然,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汉代“白描”。这与汉画像石中注重剪影式对比与程式化飞奔的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木连理,位于《五瑞图》左下方,并排画树木二株,枝干虬曲而上,较低处,两树二枝相向而生,合为一体,正所谓“连理枝”,图左题榜:“木连理”。木连理外形朴素,枝干曲升自如,随遇而安,不经意中树冠形成一个圆形。汉画石中的木连理则追求夸张效果与装饰性。
《五瑞图》右下是“甘露降”,绘一树形,树枝向上,似有露珠在滴下。树下刻画一人,姿态虔诚,低头伸臂托物接露,此便是承露人。承露人采用简笔画法,笔短意长,寥寥几笔,承露人的虔诚、憨厚便跃然壁上。此人物比例准确,情态自如,线条谙熟简劲,置之画像石中则风格别具。
嘉禾,居于“木连理”与“承露人”之间,一禾九穗,分垂两侧,果实累累,富有弹性。汉画像石中的嘉禾,“神”性十足,或与仙姑合体,或是按部盘曲。相比之下,前者率真野逸,后者富贵安详。
汉画像石考古发掘材料证明,相当一部分汉画像石墓,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墓门画像石在完成雕刻后,还要施色,使之成为彩绘画像石。例如,陕西神木大保当11号汉画像石墓右门柱画有楼阁、人物、天神、龙凤等。其中楼上一人长袍施绿色;应龙以红、墨彩相间绘鳞甲。彩绘画像石的技法大约沿用汉代壁画之工艺,以毛笔为主要绘画工具,使用朱、绿、黄、橙、紫等色调成的矿物质颜料。在绘制技巧上继承了战国以来单线平涂手法。画像石彩绘打破了画像石的单调与凝滞,使画像获得了构思、构图的理想效果。可惜这部分画像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现已无法看到当初的风采。《五瑞图》完成刻勒后是否设色,今不得而知,但仅从《五瑞图》的名称已经能感受到五彩纷呈了。
《五瑞图》作为《西狭颂》摩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插图”性质;就《五瑞图》本身而言,其图左题记及题榜则具备了题款特征。总之,《五瑞图》与《西狭颂》是珠联璧合、图文并茂的汉代石刻书画精品。由于摩崖避居陇南,而古代《西狭颂》拓本又往往遗拓画像,故《五瑞图》鲜为人知。其精湛的镌绘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必将受到更多汉画研究者和美术学者的高度重视。
(作者系甘肃省陇南师专美术设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莹)
转载旨在分享,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请扫描新闻二维码
加载更多+